文联动态
基层活动
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谈读书:我怀疑不读经典的人的判断力
还没见到王强,就听说头一天晚上的读书分享会让他有些不高兴——现场观众只问投资,没人关心他的书。
王强最大的标签是新东方联合创始人,他和俞敏洪、徐小平组成了我们常说的新东方“三驾马车”。在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中,他正是佟大为扮演的王阳这个角色的原型。
但相比于被视为成功的商人,王强更愿意被视为“读书人”和“藏书人”。
中学时代在一位特立独行的语文老师引导下,他开启了阅读的大门。进入北大英文系,身边的老三届学长和从“文革”走出来的老教授们,感染王强他们加入到这样一个全民疯狂汲养和补课的阅读时代。
这种对知识的饥饿感也让他很对“拥有”书籍有着原生的冲动。刚毕业留校,他就透支了未来三年半的工资买了两套大部头丛书。30多年里,他走遍世界各地,搜寻各种古书,收藏、阅读相得益彰。但是他从未走进拍卖行,对于从欧美等地费力搜来的古书,他也不视为商品,在他眼里,那是二流藏家干的事。
他极度厌恶畅销书,但不成想自己关于阅读的随笔集却卖得不错,刚刚由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出版。他也不喜欢营销学,但却用了“读书毁了我”这个略有标题党之嫌的书名。对此,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,王强说,毁字是在摧毁旧我、塑造新我这个意义上展开的。
访谈中,王强展现了强烈的个人意识,对自己的喜好和偏见好不掩饰,他曾放狠话说“书籍那么多,80%是垃圾”,这次又对那些拒绝阅读经典的人表达了怀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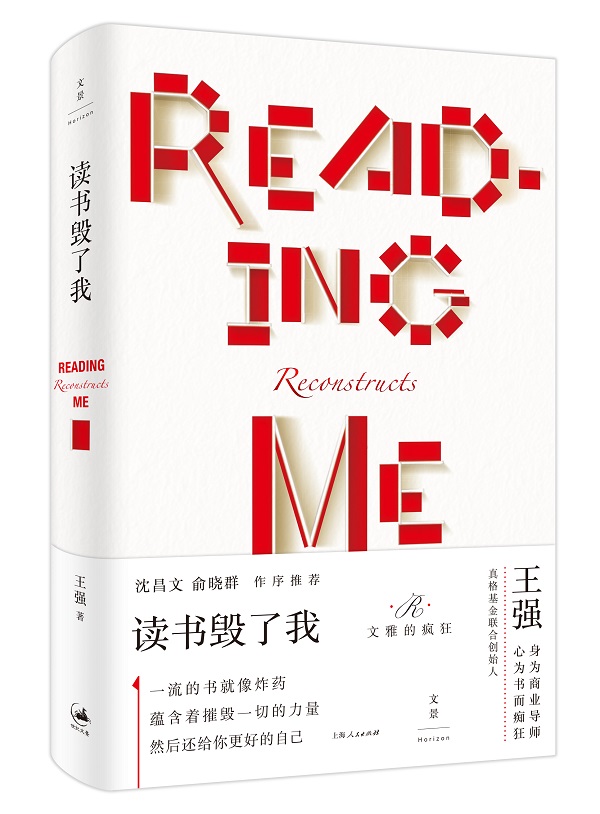
什么书是“一流的书”
澎湃新闻:《读书毁了我》书名一开始就多少被说“标题党”,这次没有想过调整吗?
王强:当时编辑徐晓给我这个标题,我也有些疑问。她就解释说,这个“毁”字,在北京话里是“团”的意思,就是你要想做成形一个东西,首先要把它团起来,先是一个非成形的状态。
我一想阅读对我人生的作用,自我的成长,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养成,就像我们做成雕塑之前,必须要把材料团起来,混成一团,这其实是“毁”的过程,而毁是为了立,也就是重塑。
正像我在印子里引用了法国哲学家阿杜的话,“有力量的文字”旨在“型塑”(to form)而不是告知(to inform) 。所以真正好的书,如果它不能打破、摧毁你过去的认知、经验和思维方式,塑造一个崭新的、开阔的自我,那这种书读不读价值不大。所以这个标题我还越来越喜欢了。
澎湃新闻:你的座右铭是“读书只读一流的书”,你的一流书标准是什么?
王强:在我看来,一流不是意味着思想绝对超前,而是一个作家的文字状态有多么纯粹。这个纯粹让我喜欢捕捉文字呈现的方式、再造的内容,构建出来的世界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,而不是东拼西凑,充斥着前人痕迹的东西。
如果一部作品看似很新,但实际上早有人珠玉在前,那这部作品哪怕再精彩也不能算是一流的。我常说先秦思想是一流的,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受其他思想方法论的影响,所以它们思想的独立性保持非常强的。所以我衡量一本书是不是一流,我看两方面,一个是纯粹性,一个是呈现方式的原创性。
澎湃新闻:对一流作品的判断实际上受个人知识结构、审美趣味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,抛开这个,是否存在客观上的一流作品呢?
王强:客观上给一流作品下个定义那我认为就是经典。经典不是某一个人、某一家出版商的意志,而是在时间长河里,几百年上千年积淀下来,一种集体无意识筛选下来的结果。这可能是客观上最接近一流的作品。
所以狭义来讲,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一流的判断,这是随着你经验、视野和审美的变化而变化的,你二十岁对一流书的判断和八十岁时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但从某种客观角度来说,在一个文化传统中,大家都认为是优秀的东西,我就认为这是相对客观性的一流标准了,否则很难写文学史了。可能会忽略掉个别优秀作家作品,但是总体上各种文学史呈现的方式是接近的,争议不大。
澎湃新闻:有些作品是无法绕过去的。
王强:对,就像柏拉图,全世界各种语种的文化都要去读,这就是经典,这就是一流的。所以尽管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一流标准,但是作为读者来说,能够给自己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,先去涉猎那些大家都认为是一流的著作,那你品味的诞生就不会偏。
如果你偏偏要拒绝这些,你们都认为是一流的我偏偏不认为,好,我同意,但是我坦率地讲,你自己审美的品位,思想的判断力、敏锐度,是否能够辨别后来不断涌现的新文字世界,我非常非常怀疑。

王强
翻译我更愿意相信已故译者
澎湃新闻:那你在阅读上有没有什么癖好,比如有些人只读最新作品,有人则说不会看去世不到20年的作家?
王强:当然,我有很多个人癖好。比如说翻译作品,我是很挑译者的。如果一部比较专门的书,比如哲学类的,译者不具有专业背景的话我是很难相信的。而文学类译作,我愿意先走进那些已故并且在世时比较高产的译者,而不愿走进现代的很年轻的快手译者,我本能地拒绝。
澎湃新闻:现在很多时候是只懂外语就去翻译了。
王强:能读原文我宁愿读原文了,不能读的我会去寻找那些已经故世的经典译者。而且最好的译者是一辈子只译一个作家,或者只译一部作品的。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,不管用现代的眼光如何争议,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从精髓上超越朱先生的翻译。
所以我说更相信已故译者,这不是变态。因为在那个商业化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,一个人选择了翻译这个冷板凳来做,这是一种生命的选择。比如李丹翻译《悲惨世界》,没翻完去世了,他的太太方于接着翻。这样穷尽两个人生命的译本,我不知道现在哪个译者敢于向他们这个译本来挑战。
现在年轻人很少有我们那代人对知识的饥饿感
澎湃新闻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藏书呢?
王强:我觉得很自然,当年书荒,得到一本书很不容易。我最早读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是在1983年,尽管北大图书馆里有,我却是在暑假内蒙古草原上读到的。
当时我们上了现代文学课后大家知道《围城》,没上完课就都去图书馆借,很快就没了。我整个一学期都没借到,因为刚一还你错过那个节点,就被别人借走了,买也买不到。
这种对书籍和知识的饥饿感现在你们年轻人是难以体会到的。比如说我读中学时,我父亲为了给我买一本英汉词典,坐火车到北京去王府井书店排了一整晚。
所以我那个学期在北大没能读到《围城》,暑假回到内蒙古草原做翻译,在一个小便利店里发现了《围城》,上面布满了尘土。所以我第一部《围城》是这样得到的。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轻易让别人拿走,就有了“拥有”的冲动,也就有了收藏的感觉。
第一次作为收藏买的是两套大部头的《胡适文集》《李敖文集》,当时我刚刚留校,在北大图书馆发现在卖这两套书,价格是3600块钱,我一个月工资120块钱,相当于三年半的工资,根本买不起。怎么办呢,我就做了最早的P2P——我就回到教工宿舍,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借钱,凑了3600块。这是我藏书的开始。
澎湃新闻:你现在藏书量是什么概念?
王强:我的书有两类,一类是供我阅读的,一类是收藏级的。收藏级的版本得是在某个领域达到了公认的标准,这个有几千种。
澎湃新闻:现在对这种收藏级图书的追求和当初收藏《围城》《胡适文集》的动力还一样吗?
王强:内核是一样的吧。因为我和其他纯粹的收藏者不一样,我还是个阅读者。不像有些人收藏了之后,束之高阁等待下次拍卖,我不会拿去拍卖。之所以买很多不同版本,我是要比较不同版本之间板式、字体等等的差异,即便再珍贵的藏书我也是要一页一页去翻看的,不会买来等着增值,那是二流藏家才做的事儿。

王强在书中一再提及的埃及作家埃德蒙·雅贝斯。
碎片化时代反而应该慢下来
澎湃新闻:每年世界读书日全国各地都有各种阅读活动,有观点认为,越是强调阅读实际上恰恰是反映我们不那么关心阅读。你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?
王强:我们进入了技术加消费的时代,每个人的兴趣点越来越多,大家越来越难以专注,深刻的、严肃的阅读越来越失去受众,似乎这是碎片化时代的潮流。大家拿着手机、智能设备,好像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多,但是没有人去深度沉浸下去。
这是一个现象,但是如果只是随波逐流的话,你只能成为大潮中的一员,而不可能成为这波浪潮中脱颖而出成就自己一点事情的人。所以反过来,当大家都追求浅、快、散的时候,你追求慢、完整、深度,似乎是逆潮流而动,但恰恰让你赢得了和别人不同的厚重。
澎湃新闻:这几天讲演结束后,提问的观众都只关心资本,鲜有人提问你的书和阅读,失望吗?
王强:我基本上不太回答这些东西。我做投资从来不读投资学方面的东西,我做新东方开始到现在,也从来不读管理学的东西。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,因为这都是信息,都是总结起来的标准化的东西,大家都知道,我再知道也只是和别人一样。
但是哲学、历史、美学这些人文的东西,它们带给我的是眼光和判断力,对我做企业也好,做投资也好,我看到的维度、层次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澎湃新闻:给读者推荐一个你钟爱的作家或作品吧。
王强:那就我在书中一再提及的埃及作家埃德蒙·雅贝斯(Edmond Jabès,1912-1991)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迄今为止看不到一个中译本(编者注:2017年始,广西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五卷《埃德蒙·雅贝斯文集》),但从我十几年前发现这个作家之后,他的作品就成为了我的案头书。
他是用法语写作的犹太思想家,作品在文类上很难归类,你很难断定他的作品是诗,还是散文,还是哲学,还是宗教思考,但是又深邃又美丽,每次读让我心都砰砰直跳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