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联动态
基层活动
《瞻对:两百年康巴传奇》一部川属藏民的精神秘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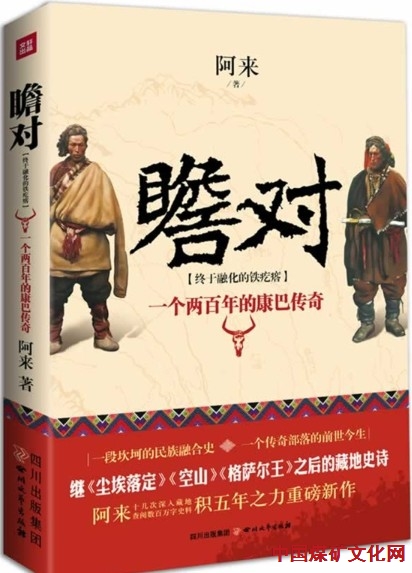
阿来是一个既有诗人禀赋又不乏学者气质的作家。他总是像猎手那样独来独往,永远游走在文坛的热点之外。对他来说,写作似乎就是要解决自我存在的终极命题——我从哪儿来,将往何处去。所以,多年来,他始终执着于藏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。尤其是面对哺育他的康巴地区之川属藏族文化,他几乎表现出某种痴迷的状态。从《尘埃落定》到《空山》,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明。
或许仅以小说方式,还难以传达自己对于这块土地的感知与思考,也不足以有效梳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,于是,阿来又动用了非虚构式的写作,从历史的缝隙深处,不断寻找有关川属藏民的生活记忆,并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《瞻对:两百年康巴传奇》(刊于《人民文学》2013年第八期)。这部作品以一个瞻对土司部落为载体,追述了该土司自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变迁,重构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艰难而又独特的生存境域,并借此传达了阿来对于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。
康巴藏民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茶马古道之上,扼守着川藏交通的要塞。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影响,他们既不同于西藏地区的藏民,又迥异于川西的汉民。不错,他们同样信奉藏传佛教,但他们又常常游离于宗教之外。阿来就是从这种存在入手,精心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“瞻对”土司作为考察对象,从微观史着眼,以一个小小土司的兴衰,不动声色地踅入历史深处,复活了康巴藏民复杂而又坎坷的记忆。用阿来自己的话说:“我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,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,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,一个典型样本。”
历史从来都是以具象的方式,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。阿来选择具有“缩影”意味的“瞻对”土司作为考察目标,就是为了立足于具象化的历史现场,见微知著,由点及面,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中,再现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。所以,在阿来的笔下,我们看到,“瞻对”是一个并不安于现状、雄心勃勃、桀骜不驯的土司。他们居住于深山巨壑之中,却从未享受过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安详,而是被各种历史动荡和权力诱惑不断夹击,以至于不得不卷入波诡云谲的历史之中,以自己特有的方式,向各种坚硬的现实发出艰难的挑战。
这种挑战,以最为常见的方式体现出来,便是“夹坝”行为。在阿来的少年时代,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便会在腰带上斜插一把长刀,牛皮做鞘,刀出鞘,宽约三四寸,长二三尺,寒光闪闪,刃口锋利。在阿来家乡的方言中,这种刀就被称为“夹坝”。后来,这个词演绎为“强盗”的意思。阿来出生的山村,在一处深沟之口,往深沟里去十来里,有一片黑森林,传闻过去便是夹坝出没、劫掠过往行商之处。阿来成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翻越雪山的公路早已通车,驿道早已荒芜,行商绝迹。这样的时代,夹坝自然失去生存的土壤,空留下一种刀名。后来,穿着风气也日渐变化,家乡的男人们大都换下宽袍大袖的藏装,改成短打,没有实用价值的刀也从生活中渐渐隐退,仅仅留存在书页的文字中了。
瞻对一地,山高水寒,林深路长,时有刀光剑影,自然适于夹坝生存。很多时候,土司对于夹坝的滋扰无可奈何,甚至有的夹坝行为还是当地一些土司组织实施或纵容指使的结果。但凡夹坝出没之地,生产力极度低下, 百姓要承受物税与无偿劳役,于是,在这些地方,夹坝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,或者说是对生产力不足的一种补充。有清一代,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,朝廷和地方当局为此煞费苦心。阿来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,牢牢抓住了这个充满吊诡色彩的词汇,一方面借助浩繁卷帙的历史文献,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中,逐一呈现上至中央、下至地方各权力部门对瞻对“劫盗”行为的讨伐;另一方面,又通过田野走访与神秘化的宗教思维,重构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、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,再现了他们的“游侠”气质。阿来以鲜活的笔墨还原了历史,还原了瞻对部落的复杂与矛盾,从而统一了后来者从不同历史视角对其所形成的对立性的片面评价。
有趣的是,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历史中,从清廷官兵、西部军阀、国民党军队,到西藏宗教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等,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个弹丸之地,为这块边远贫穷之地带来现代文明,也搅得这里风生水起。仅以清朝为例,历史文献表明,每一次对“夹坝”的围剿不仅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,而且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。为此,他们一次次调动八旗精兵远赴川西,派遣钦差大臣,可谓绞尽脑汁且又费尽时力,但结果是,面对仅万余人的瞻对部落,每一次都不得其终。
虽然阿来没有动用虚构的笔墨,再现一代代大清皇帝的尴尬和无奈,但是,清廷统治的无能和衰败,却已显露无遗。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,也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,如鹿传霖就提出“改土归流”的设想,结果遭到去职;凤全想继续改革,又命丧理塘;赵尔丰胸怀“治边六策”,与西藏张荫棠、联豫励精图治,“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闷,局面焕然一新”,然而又碰上辛亥革命,最终丧命于军阀刀下。民国来了。虽有“五族共和”的口号和梦想,然而在川属藏区,清朝留下的边军,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,受英国支持的藏军,以及一些被废除的土司自行恢复的武装,大寺院自行组织的武装等等,再度使这里战事频仍。直到1932年,刘文辉部击败藏军,这片土地才渐趋平静。
1950年,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,未经战斗就解放了整个瞻化(1916年更名为瞻化县)。这个历史上极其“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”,两百多年的“夹坝”纠葛,从此渐渐消解。
新中国成立后,瞻化县又更名为新龙县。“现在去新龙,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,驱车西经道孚县、炉霍县、甘孜县,再转而南下,大半日之内,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。”阿来写道。两百年前的瞻对藏民不会想到,从县城出去,乡乡都有公路相通,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。在酒店茶楼, 远来客和当地人,讲的都是如何发展藏区,开发藏地,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。而有趣的是,这些旅游资源,就是当年清军难以克服的险山要隘与深峡,以及那些石头垒砌、形式古雅的碉寨。当地人甚至希望从强悍民风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资源,以康巴来命名。可惜这一名字已被他人注册。退而求其次,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的名字:康巴红。这个红,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,也是英雄红。
走出文字意义上的瞻对历史记录和解读,在民间,可以听到瞻对人民更加丰富、彪悍、勇猛、不屈的精神记忆。通过一次次的走访和调查,阿来渐渐发现,那些部落首领,在瞻对人的心中常常以神魔混杂的形象,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之中,无论是班滚、贡布郎加,还是青梅志玛,都是如此。它让人们看到,在这片土地上,“一个人常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”,一个是现实的世俗世界,另一个则是充满传奇的心灵世界,在那里,“人们仍然在传说种种神奇至极的故事,关于高僧的法力,关于因果报应,关于人的宿命。”
无论传奇还是现实,也无论“劫盗”还是“游侠”,在两百多年的沧桑记忆中,瞻对只是一个方寸之地,虽然他们偏居一隅,看似远离了时代中心,却又每每被历史中的各种力量吸入巨大的漩涡之中,承受了无数的大灾大难。各种图谋与觊觎,不断地利用瞻对之地较智较力,从而使瞻对浓缩成一个特殊的历史范本。当然,对于阿来而言,解读这个范本,固然是想破除简单的历史进步论思想,同时还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藏区平民的超乎客观的各种想象。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各种冲突中反复盘旋,所谓“文明一来,野蛮社会立时如汤化雪一般,土崩瓦解”,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。
更重要的是,阿来还告诫人们,“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,认为藏区是人人淡泊物欲、虔心向佛、民风纯善的天堂。持这种迷思者,一种是善良天真的,见到社会中某些物欲横流的现象,于是认为生活在别处,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;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,却故意捏造虚伪幻象,是否别有用心,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。”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,他永远无法脱离自身环境而活在纯粹的理想之中。
一个民风雄强、号称铁疙瘩的部落,已经散落在记忆深处;一段漫长、复杂而坎坷的民族纠葛史,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作为川属藏民的后代,阿来通过自己的反思和重审,再度重构了这段历史。它是瞻对的精神秘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秘史。
(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




